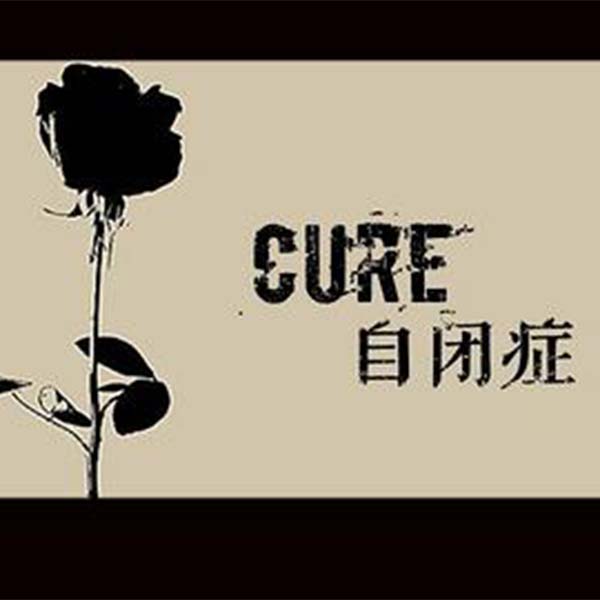37岁自闭症儿童楠楠妈妈自述 <关爱自闭症儿童>
但是,只要你认真教他,他还是能学到东西的。
为了帮助自闭症儿童和家庭,一些城市的启智学校已经将职业教育纳入教育和康复体系。初中毕业后,孩子们可以学习七门职业课程,包括中式糕点、西餐、洗衣和洗车。
独立生活,能够自理,有一技之长,自力更生,是每个父母对孩子最基本的愿望。
比如系鞋带,对很多自闭症孩子来说就是一个难点。一开始我们教了很久,楠楠就是学不会,让孩子发脾气,我们都要崩溃了。
无奈之下,我们带着孩子去北京检查。确诊后,我们被告知他们是自闭症。听到这个诊断,我们感觉像是晴天霹雳,一箭穿心。我们真的想和我们的孩子一起结束我们的生命...但是没有任何专业机构和专业知识的支持,只能慢慢摸索着给孩子干预。
虽然没有专业知识支持他,但是我们观察了他,得出了一个道理:他虽然各方面远远落后于同龄人,但是智力水平比较低。
在几位爱心老师的培养下,他学习了声乐、朗诵、太极拳等才艺,多次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省市电视台为观众表演(还担任过声乐老师的小助手)。
绝望的是,这个城市几乎每家书店都买不到一本关于自闭症的书。
那时候,我们渴望有专业的知识,专业的机构,专业的老师来帮助我们的孩子。因为我们对如何训练他一无所知。
直到孩子十多岁,我们才终于在当地开了第一家自闭症机构。我们第一时间报了名,想让他尝试接受专业的康复训练。没想到,我们又一次被拒绝了,因为我们“年龄太大”——机构只接收学龄前儿童,没有能力帮助大一点的孩子。
被拒绝了几次,或者被欺负了,我们别无选择,只能退学。事实也很清楚:只要父母不放弃,孩子就有希望。
另外,每次编完故事后,我们都会用夸张的方式讲给他听,以引起他的注意。慢慢的,他再也不喜欢听故事了,但是整个过程极其漫长。
目前,楠楠和本市一些大龄自闭症残疾青年一样,都有一个公益岗位(由残联安排)。这个岗位不累,每个月发少量工资和社保。
比如他小时候喜欢看电视广告或者天气预报,我们就在自己的小故事里加入广告和天气预报。就这样,我们一讲故事,他就开心地跑过来,达到了提高注意力和喜欢听故事能力的目的。
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培养他看电视剧的习惯,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每天吃饭的时候看电视剧,我们陪他看,给他讲解剧情,逐渐帮助他理解别人在说什么。
当我拿到这本厚厚的书后,当时就傻眼了,因为里面几乎都是介绍自闭症的症状和训练内容。我孩子那时候10多岁了,这本书对我没用!我手里拿着我经历磨难后的第一本自闭症书,真的想哭。
后来他长大了,我们就训练他看一些儿童读物,比如绘本或者动漫书。
第一,只是给孩子吃饱穿暖,没有任何训练,只由一个“傻子”抚养,本质上是一种变相的放弃;另一个是破釜沉舟。我们会自己去干预和训练孩子,努力引导他走出孤独。后一种选择无疑会给我们的身体、心灵和经济带来巨大的压力,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孩子以后能否康复成功。
他小的时候,我们多次送他去公立和私立幼儿园。但是,没有一个幼儿园可以待很久,几天之内就会被退学。因为老师们都说:“我们没见过这样的孩子,不能带。”
当时我们很清楚,儿子在能力上和同龄人(其实比当时的同学大1-2岁)有很大的差距,但如果不硬着头皮让他上学,他这辈子都不会有上学的机会。
在学校,他没有任何朋友。就算别人欺负他,他也不会告诉老师或者父母。被人欺负后,他不会还手。他只能被别人欺负,连老师都为他着急。
电视剧就相当于一个小世界,各种各样的人物和场景。通过看电视剧让孩子用自己的方式去理解,让孩子更好的融入社会。
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父母也一天天变老,留给我们的时间越来越少,但他们仍然要面对培养大龄孩子、没有机构、短时间内找不到正式工作等挑战——这是所有大龄自闭症患者父母所担心的。
但是当时国内大部分医生对“自闭症”(孤独症)还没有完全了解,我们带着他跑遍了城市的各大医院,却没有办法得到明确的诊断。
基于这种想法,我们认为,要想让他“说话”,首先要训练他“听懂”,然后让他一点一点地试着说简单的话。
就连他的声乐老师都说,我儿子的语言能力是他接触过的所有自闭症孩子中最好的。
“我儿子已经37岁了。他小时候在语言、情感、社交等方面都有很大的障碍。而且他不仅自闭,还伴有多动、智障等。按照现在的标准,他肯定是重度自闭症。”
语言障碍是大多数自闭症孩子面临的问题,楠楠也是。
另一方面,大龄自闭症者缺乏干预训练机构,这也是中国所有大龄自闭症家庭都苦恼的问题。
我们一度以为他是个聋哑孩子。带他去医院检查后,医生说他不是聋哑人。过了一会儿,他开始说话了,但他只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跳出来,完全说不出一个字。
回想起来,我们培养他30年,都是在家里。经过30多年的艰苦干预,我们找到了一条让楠楠从对自闭症一无所知成长起来的路。
同时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楠楠注意力不集中,总是走神,不愿意听别人说话。
目前他是我市年龄较大的自闭症儿童之一,也是能力较高的一个。在自理、家务、学习天赋等方面都还不错。
无奈之下,只能求助于书籍。
对于这些大龄自闭症儿童来说,已经有了一些生活保障。但在我们当地,最近已经下发文件,三年后将取消所有残疾人公益性岗位。
现在,他可以和人顺畅对话,一个人出去逛街,交水电费,去社区处理残疾人事务,接受记者采访等等。
在整个训练过程中,没有资料,也没有人可以帮助我们,只能自己动手,自己摸索,自己积累,所以我们制定了一些被认为可行的,适合孩子实际情况的干预方法。例如:
所以很多大龄父母都期待有一个专业的针对大龄孩子的培训机构,可以让孩子各方面的能力不断提升和升级。
直到7岁,到了上小学的时候,他的语言能力还是很差。
南上小学后,我们开始摸索训练他。但是因为当时的条件和环境的影响,孩子的接受能力比同龄人差很多,所以只能循序渐进,能力弱在哪方面都会培养。
我们把他送到了很多学校(包括他小时候的很多幼儿园),直到他八岁,但是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拒绝接受孩子与同龄人不同的行为和无法与人交流的表现。
我们年轻的自闭症父母,尤其是那些孩子高功能或恢复良好的父母,都希望他们的孩子根据自己的实际能力在社会上找到一份工作,能够自力更生。
由于我们夫妻在文革时期都是农村知青,那时候大学不招生,我们只能在农村工作,根本没有机会上大学。回到市里工作后,两人都将近30岁了。但我们两个都很努力,一边工作一边上大学,过着向上而充实的生活。
一开始我们也试着给他讲一些儿童故事,他完全听不懂。他甚至不知道“听故事”是什么意思,只能自己编一些简单的故事。
但是一切都有回报。经过这么多年的干预训练,现在孩子的干预已经很好了。现在我们夫妻虽然退休金不多,但加上医药费(我俩都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等费用,常年需要吃药,入不敷出。
因为孩子疾病的特殊性,教育他的方法不能和他的年龄相匹配。
我的孩子出生于1985年。
提高自闭症儿童的能力,让孩子入园,融入;帮助自闭症儿童掌握技能,让孩子找到就业出路;推进社会救助体系,让自闭症群体未来有“信任感”。以上都是父母的期望,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经济压力方面,为了陪伴和干涉我们的孩子,夫妻俩都40多岁辞职了。辞职离开单位照顾孩子20多年的生活压力真的不小。
那时候,我们仿佛在一座孤岛上,孤立无援。
但是,当孩子一岁左右的时候,我们发现他在很多地方都落后于其他同龄的孩子,比如说话晚,走路晚,对亲戚冷淡等等。事实上,他符合自闭症的几乎所有核心症状。
至此,我们的疑惑越来越深,探究真相的欲望也越来越强烈:孩子一定是得了某种病,但到底是什么病呢?为什么会有这些症状?没人能告诉我们能不能去上学。
尽管越来越多的人了解自闭症,越来越多的人愿意理解和包容自闭症儿童,但“就业”和“关爱”这两个问题对他们来说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看病十年,只能在家干预。与其干预,不如在黑暗中摸索,陪伴孩子成长。
所以,我们只能硬着头皮,提心吊胆的送他去小学。入学后,事实很清楚。因为他不能理解和表达自己,各方面能力都很弱,经常出现各种状况,没有朋友,被欺负。最后,他只能在小学毕业前提前离校。
当时国外一些先进的理念和方法还没有传入国内,网络也没有今天这么发达,所以我们没有资料可以参考,也没有老师、医生、机构帮我们指导。
这时,孩子的父亲突然想到,系鞋带需要几个步骤,对自闭症孩子来说确实很难,于是我们改变了教学方法,分解步骤,反复掌握每一步,才进行下一步。就这样,楠楠终于学会了系鞋带。
但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当时对孩子的干预方法和现在机构、专家说的一些方法不谋而合。这说明我们当时走的路基本是对的。
比如他当时虽然八岁,但是智商和能力只相当于三四岁的孩子,所以只能降低任务要求。
有一次,一个同事的老公去日本,我赶紧让他帮我买了一本自闭症训练书。他真的帮我买了纯日文的书,回国后没日没夜的帮我翻译。
他从来不看我们。甚至当我们叫他的名字时,他也不回答,就好像没听见一样。我们一点也不亲密,我们没有拥抱或粘人。甚至在我伤心哭泣的时候,他也无动于衷,只在一个地方自言自语,无缘无故的笑。面对他的冷漠,我们焦虑,愤怒,更多的是无奈。
自闭症患者需要终身干预训练,但目前国内绝大多数的训练机构都是针对幼儿的,能够帮助大龄青年的机构几乎没有。
从动画片开始,边看边说,然后逐渐转为简单的电视剧(比如农村生活的电影),一点一点培养他说话。
无独有偶,在大连自闭症综合服务中心,也为自闭症儿童设立了辅助就业基地。经过学习和训练,孩子可以完成蛋黄酥、雪花蛋糕、面包等订单的制作,拥有一项可以养活自己的技能。
此外,一些学校将实验教室搬进了商场。在全景教学教室里,学生可以努力做清洁、摆放物品等简单的工作,也可以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会与客人进行简单的对话和交流,传递物品。
在他愿意听故事的开始,我们试着加了几个简单的问题;后来,让他复述故事;最后,我们一起讨论故事的内容等等。这些都是为了提高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一步步来的。
关爱自闭症,我们永远在路上!今年的42自闭症关注日由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自闭症康复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北大医脑健康承办的2022世界自闭症日数字医疗展望峰会在北京举行。在此期间,我们发布了《2021发育障碍儿童康复行业蓝皮书》,呼吁更多社会力量以实际行动关注和帮助自闭症群体。
简而言之,这是我们自己在和孩子进行干预的过程中总结出来的。
上世纪80年代,国内医学界刚刚引入“自闭症”的概念,对这种疾病的认识还不够深入,普通大众也极为陌生,更不用说专业的康复机构了。
作为一个大龄自闭症儿童的家长,我想说,回顾过去的37年,困难和挑战几乎是一个一个坎。
父母,未来还是有希望的,不要放弃!干预,干预,把握黄金干预期,一切“演习”只为明天不“断链”。
现在的孩子,从一个什么都不会的重度自闭症孩子,逐渐学会了购物、做饭、洗衣服、打扫卫生(包括个人卫生和家庭卫生)、独立出门坐公交、地铁、打车、独立在火车站买票、等车、酒店入住、陪父母看病、药店买药、交水、电、气等等。
这是楠楠妈妈的自述,一个37岁的自闭症孩子。
学校不收,我们只好咬牙送他上小学,要求学校陪读。学校的回答是:如果能独立上学,可以试试。绝对不允许家长陪他上学。
夫妻二人经过反复分析研究,认为孩子语言表达能力差的原因是他听不懂话,不愿意听别人说话,以至于更不可能听懂别人的话。如果他听不懂别人说的话,他自己怎么说呢?

- 发表评论
-
- 最新评论 进入详细评论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