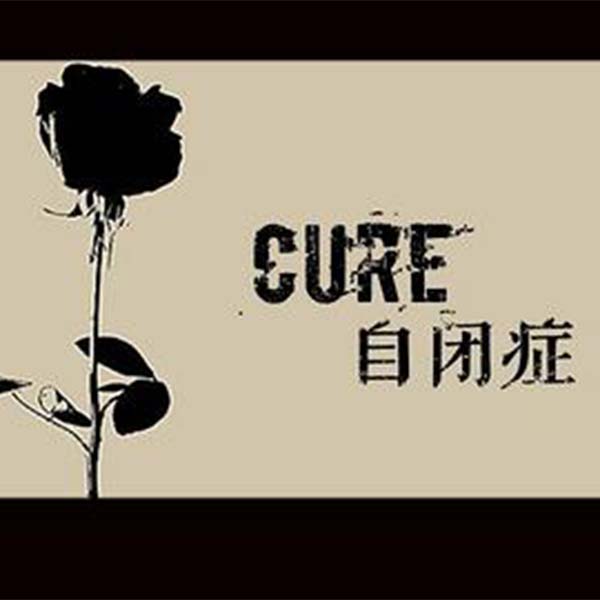Mainland China自闭症公益组织:父母的自救之路 [自闭症的症状]
BestBuddies代表了一个融合、平等和非歧视的社会。王晓甚至在留言中告诉自己,以前作为父母,他关心的是孩子如何生活,即如何吃饭和穿暖和的衣服。他一个人交普通朋友是不可想象的。儿子的改变让她意识到,一个同样有障碍的人,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生活状态、自信心、能力、价值可以如此不同。
“尤其是父母创办的机构,有些没有很好的定位和分工。”星星雨的执行董事孙将描述为机构负责人的俱乐部。除了传递公益和社会服务的理念价值,还需要训练很多机构的能力,比如资金筹集、资产公开、董事会等。
还有一些更长远的目标。王小庚一直希望把她在美国看到的BestBuddies项目搬到中国。这是一个提倡全纳教育的社会。它将志愿者与我们学校有特殊需要的学生联系起来,成为朋友,一起旅行,跳舞,看电影,在一年内到披萨店吃晚餐来筹集资金。
照顾自闭症儿童是一项非常需要耐心的工作。她要求面试者做一周的志愿者,在此期间大约有一半的面试者会放弃。持之以恒的教师要经过组织内外的培训,试用,考试合格,才能正式入职。从培训开始,星冉中心就要承担老师们的工资,收支不平衡一直困扰着陈力。
“我们所有的收入只能维持老师的工资。我们的水电煤气中餐费用都是我去外面筹钱。如果我养不了,我就自己掏钱。去年一年,我亏了9万多。”陈丽说,除了过去做生意的积蓄,有时候自己的工资和老公的收入也要投入到事业单位。
场地也困扰着长春的“天使之家”家长联合中心。这家由张和李磊开办的机构,开展“社会化”康复训练,需要一个单独的房间,避免孩子的互动。他们一年内搬了几次家,为的是找到合适的、负担得起的空间。最新的落脚点是社区免费提供的活动中心。他们又租了一套公寓来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尽管经历了波折,张对最终的结果还是很满意。他一直希望自闭症机构能够走进社区,促进不同人群之间的相互了解,探索社区融合的新模式。
公益的土壤还在培育中。一个明显的区别是,国外的公益组织有大量的公众捐赠,而国内的公益组织更多的依靠基金会资助和政府购买服务。企业家也逐渐关注公益,但也有人与一线公益组织的理念有分歧。曾经有个老板在长春资助天使之家,但是机构满足不了投资人快速成长的想法,双方只好和平分手。
负责自闭症资助项目“海洋天堂计划”的壹基金联合公益部主任任估计,2005年,中国只有几百家公益服务机构,现在可能有8000多家。
北京房租贵她印象深刻,但两次干预效果也很明显。不是所有的家庭都能负担得起异地生活。回到家里,其他看到孩子变化的家长也希望陈力成立康复机构。在家人的支持下,2020年底,她在平江县注册了星冉特殊儿童康复中心,开始在周边乡镇招收智障儿童。
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前的几年里,任前往许多城市,与他在世界各地的“兄弟姐妹”会面,讨论他们需要什么样的支持。会后他们会在房间里聊到深夜,聊起带孩子的艰难和新的事情和想法。
为了扩大智障儿童的生活半径,回国后,王小庚和14名智障儿童的家长成立了智障儿童家庭支持中心,并于2014年启动了整合中国智障儿童家长组织网络项目。他们试图在中国推广BestBuddies模式的融入活动,通过文体活动、兴趣小组、家长的喘息和培训,甚至融入教育和支持性就业试点,让智障人士成为“自觉、自立、独立的年轻人,有效地参与和融入现实社会,建立自己独立的社会角色”。
经过近两年的训练,她已经能“擦着脸,什么都不怕”了。她学会了找领导和爱心人士,解释精神障碍家庭的经历和困难,需要什么帮助。“作为康复机构,如果不提倡,会很困难。”她说。
但孙也看到,随着互联网公益的兴起,资源不再只集中在北上广,中小机构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现在真的很难。也可能与这两年的经济环境有关,公众缺乏信任和参与,”但他也认为,“筹款是一个机构的核心能力,它(考验)是否能真正解决社会问题,带来影响和改变。”
某种程度上,自闭症可以看作是衡量社会文明的标尺。特殊人群面临的发展障碍可以通过医疗干预来缓解;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社会如何对待这些群体。理想状态下,他们应该得到各方面的支持,消除歧视和障碍,参与社会生活,然后成长为独立自由的人。
类似的困境出现在很多机构。而筹款场地的压力往往让曾应付不过来。在她的理想中,中心应该有一个固定、宽敞、明亮的空间,供家人学习交流。“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会到一个普通的家里哭,这样情感联系就建立起来了,”她说。现在,她不得不向社区大学和其他机构借用临时场地来举办活动。“飘着呢,没有家的感觉。”
转账发生在2018年9月12日。曾惠玲接到一个电话,通知她可以去取户口本。她把这个组织命名为岳阳市智障人士父母互助中心,意思是“先天下之忧,后天下之乐”。巧合的是,这一天也是王小庚女士逝世一周年。
任举例,在一些合作较好的城市,政府部门甚至为家长组织开辟了办公场所,方便相互沟通协调,进而起到示范作用,推动其他城市的进步。孙也谈到希望各地已经有一些有一定体量的机构,可以形成一个区域网络,支持县级三四线城市小机构的发展。
陈力主管着这样一家公益康复机构。他们不仅提供可以由政府补贴的康复训练课程,还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低价的一对一课程。
但这些公益机构大多集中在一二线城市,任估计只有10%左右下沉到三四线城市。这也意味着,当许多新兴机构专注于服务时,一个定位于农村地区的机构往往不得不同时具备两种功能,并面临更多挑战。
自闭症儿童坐在窗台上看着窗外。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在此之前,曾曾因申请成立社团未获批准而心灰意冷了一段时间。年会结束后,她一周去政府部门五次,就像打了鸡血一样,终于拿到了所有的报名资料。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她反复和民政部门讨论组织的名称和形式,不断向领导宣传家长开展的活动,希望建立信任。期间民政部门也经历了人员轮换,一个比较年轻的科长接手了这个事情的管理。
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如今的公益性康复机构逐渐告别了家长自助的模式,很多都是由专业的康复专科医生开设的。随着商业康复机构的兴起,许多中低收入家庭有机会以公益机构可承受的价格享受到个性化服务。另一个关键变化发生在2014年前后。随着康复资源不再稀缺,各地陆续出现了类似岳阳优乐这样的家长组织,通过调动家长的积极性,为自闭症儿童寻求当地的各种资源。
但是在一个不太了解自闭症的社会,这些社会组织把希望寄托在了很多家庭身上。例如,为自闭症儿童提供公共价格的康复干预,可以促进更具包容性的社会环境,使儿童不必躲在家里。2008年,当一个公共基金会开始支持自闭症公益组织时,只有少数几个符合资助标准。今天,几个自闭症相关的支持网络正在全国各地孵化地方机构。
这也是业内家长组织的期待。当康复机构走向专业化、垂直化,任理想中的母组织可以起到强大的倡导作用,让行业更加系统化、正规化,帮助初诊家庭找到合适的资源,让公众了解自闭症群体,进而加大当地职能部门的重视,落实和出台扶持性的公共政策。
这五年,儿子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在他们的身上,他们看到了原本普通的儿童和青少年,他们能给我们精神障碍者想都不敢想的东西。所以,希望BestBuddies早日出现在中国。当时我就觉得,对于精神障碍家庭来说,这是一个特别幸福的时刻。”她在告别信中说。
今年(2017年)发生了几起让自闭症家庭心碎的社会事件。于是,自闭症被外界所知,很多人开始呼吁系统的支持措施。今年6月,曾在参加智障人士家长组织网络年会时,更多地听到了王小庚的声音。这些经历让她重新感受到了使命感,她决定继续推动成立一个本地的母组织,而不是等一个“有能力有资源”的人。
在20分钟关于编制的磋商中,领导一直在试图说服她放弃这个想法。最后,在曾的坚持下,领导拿出一张纸,写下了申请社会组织需要的材料。
很多关注智障人士的公益组织都有类似经历。
获得“合法身份”意味着父母拥有了公开公共资源的钥匙。此后,曾逐渐向民政、残联、教育等部门以及高校团委、地方媒体申请支持。
在乡镇办机构有很多优势。陈力说,相对熟悉的邻里关系,让周围的人了解自闭症儿童,避免很多误解和纠纷,增加孩子亲近社会的机会。城市里的机构往往对场地很头疼,而农村一般都有大面积的自建房。但缺点也很明显,几乎所有的工作都要从零开始。
她反复提到“做母亲很难”。那是一个忙碌的夜晚。她在客厅加班,老公在卧室加班。对于在城市另一端的曾来说,这也是一个忙碌的夜晚。
对于特别困难的家庭,几个机构都要想办法帮他们筹集资金。99公益日每年都是这些机构的主战场,但是几年下来,大家都觉得累了。
第一次筹钱对很多人来说都是难忘的经历。“这很尴尬,有些人很好奇你这个商人是怎么来找我融资的,”陈力说。“有时候我只是一笑而过。”她第一次为世界自闭症日筹款,却处处碰壁。无能为力,在政府工作的邻居寄了8000元。
晚上,曾带着孩子进了民政局的小楼。她抑制住紧张的情绪,敲开了5楼社会组织登记管理部的办公室。一位年长的领导接待了她,也许对她的突然来访感到惊讶。领导用略带“距离感”的语气询问她的目的。这是曾第一次与政府打交道。她想做一件当地没人做过的事,申请成立一个关注智障人士的家长组织。
“事实明,一个智障者不必因为自己的残疾而限制自己的生活内容和生活方式。在一定的支持下,他可以享有所有人的所有权利。”当时她特别提到,没有特殊的组织支持,智障人士是无法跨越鸿沟到达友谊的彼岸的。
近年来,国家对智障群体的政策或多或少与公益组织的政策倡导有关。在地方层面,一些更个性化的政策也需要当地家长来推动。
上世纪90年代,自闭症儿童家长成立了中国第一批公益组织,旨在填补中国诊断康复领域的空白。随后几年,北京、山东、广东等地的机构培训了源源不断的家长,教他们如何在家完成孩子的康复训练和教育。这些父母回到家乡后,为了帮助更多当地的孩子,也开始创办公益康复机构。
创始父母的热情投入和公益组织的长期稳定发展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张力。在看到越来越多的学生进入公益领域后,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院在2005年发起了“心联盟自闭症网络”,并开始做行业培训。星星雨成立于1993年,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自闭症服务机构。
2010年回国后,王晓意识到了儿子处境的差距。这位“温柔而强大”的女士决定倡导那些理念,改善中国智障人士的生活环境。这些努力一直持续到七年后她因病去世。说到她的遗愿,她还是放不下27岁的儿子。她希望“我们这个团体”继续为她的孩子争取权利。
教师首当其冲。即使在一些大城市,要找到一个稳定的专业治疗师也不容易。在陈力的家乡,这几乎是空白。星冉中心的老师大多来自一家已经关停的教培机构。陈力承诺的“五险”在当地很有吸引力,但要找到合适的老师还是要经过一番筛选。
没有人能拒绝说“为了孩子”。在中国,有相当一部分自闭症公益组织是由家长成立的。这是一个充满“战斗力”的群体。为了孩子,可以背井离乡去培训,也可以走进陌生的政府机关,试图说服官员给钱,给政策,批准他们成立一个社会组织。
此外,国内现有的扶持政策多针对个人,家庭是关键的照顾者和支持者。一些人认为,政策应适当回应受残疾影响的家庭成员的需求,包括支持护理者和减轻家庭护理负担。
曾的想法来自中国的先驱,王小庚,他被称为精神疾病倡导者的领袖。当一名外交官的丈夫驻扎在美国时,王晓看到了一个自闭症患者,也就是她的儿子可能到来的可能性:他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选择,并出去交朋友。换句话说,“在一定的支持下,他可以享受所有人的所有权利”,而不是躲在家里与世隔绝。
4月2日是联合国确定的世界自闭症日。今年中国的主题是“构建社会保障机制,促进服务机构高质量发展”。公益还是一个需要细心呵护的行业。虽然机会和资源在增加,但许多小组织仍然面临着传统问题的挑战,如筹资、人才、宣传、运营以及与政府建立信任。但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看到,那些关于公共社会的观念,在一代又一代的父母中循环,在各地生根发芽。
曾经,她的孩子患有严重的自闭症。因为很难照看,时间长了保姆就会不干了,于是她就成了全职妈妈。2017年和2018年,她两次带着孩子去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院寻求干预,接受家长培训。
淮南向日葵启智培训学校接受所有自闭症儿童。新华社
这些先行者的能量,支撑着公益的理念在无数普通家长中生根发芽。在4月2日前夕的采访中,陈力也谈到了这些温暖的希望。晚上9点孩子入睡后,是为数不多的可以完全处理工作的时候。有时她会怀念生孩子前做服装生意的时光。那时候,好放松。店里请了人,她可以睡到日上三竿才起床。
最近,该行业重点宣传成人康复机构、特殊需求信托和家庭支持政策。目前,我国还没有针对成年自闭症患者的政策和措施。随着第一批自闭症儿童的成长,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社会支持系统。与此同时,初为人父母的年纪也大了,要考虑百年后把孩子托付给谁。

- 发表评论
-
- 最新评论 进入详细评论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