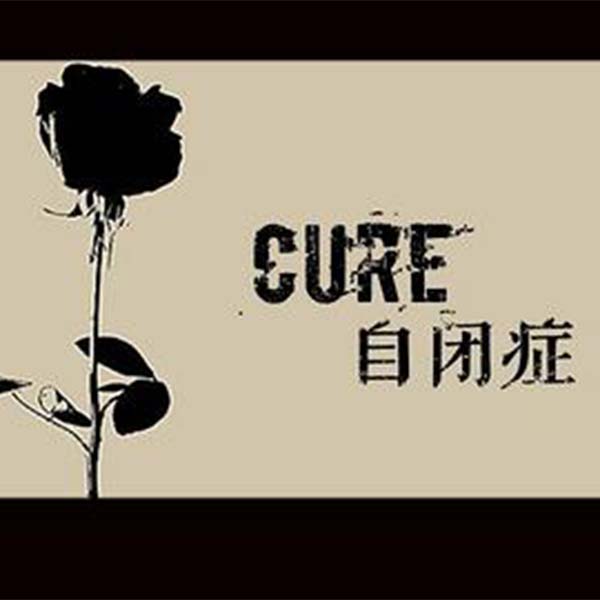了解一点自闭症的历史。 [感觉统合失调]
随便举个例子。今年2月,郭延庆博士的《老人的理念:从理论到实践》即将在付梓出版,这标志着亦氏的理念“也将从原来的个人感受和一个家庭的看法,转变为父母的‘终身康复教育指南’,启迪父母,帮助父母。也是“引进、消化、创新”的结果,经历了“理论—实践—理论”的循环和完善。其“今天的训练必须包含未来的需求,未来的目标必须在今天训练”的理念,本身就源于中国的实践,服务于中国的家长,与杨小玲教授为自闭症儿童的一生做准备的理念一脉相承。
历史是一面镜子。纵观自闭症80年的历史,“人们永远不能忘记,这些发展背后最重要的驱动力是自闭症儿童的父母(包括祖父母)推动科学研究以帮助他们的孩子并提供服务设施的强烈决心。”(罗娜·文)
以史为鉴,可以少走弯路。在引进国外理念和技术的同时,充分认识和实事求是地评价中国与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差距,总结我国父母和专业人士几十年来积累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在当前尤为重要。
我们感激洛娜。在她和全球几代父母的努力下,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对自闭症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改变。自闭症已经从一个曾经让家庭蒙羞的诊断变成了一个被社会广泛接受的症状,其被关注和倡导的程度超过了其他很多疾病。中国父母虽然起步晚了近40年,但能够少走最大的弯路,这是幸运的。从维生素疗法,拥抱疗法等。到三联疫苗理论盛行并引起激烈争论的那些年,洛娜总是以务实科学家的审慎态度冷静对待。她反复告诫我们不要盲目跟风。“我从来不认为任何东西是万能的,……我们一定不能被现有的各种治疗方法等误导。没有证据支持这些东西的功效”。她指出:“真正的进步是,人们知道如何创造一个环境,创造一个可以最小化障碍、最大化开发潜在能力的日常计划。”
经过7年的实践,也经过了近7年家长的检验。虽然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但相信也会适用于全世界的自闭症家庭。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民族自信。毋庸讳言,它还需要并将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而不是盲从,吸收消化创新才是民族自信的体现。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这一代的父母和专业人士一直以引进外国文学、理论和实践来帮助自闭症儿童及其家庭为己任。但我对几十年来探索和总结地方经验的专业人士情有独钟,对他们怀有深深的敬意。比如国内最早探索融合教育方式方法的本土专家王国光;比如提出了“给自闭症孩子立规矩”这么有见地的贾博士。我很高兴地称赞它。
今天,绝大多数在自闭症领域工作的研究人员和从业者都有着强烈的愿望去帮助自闭症患者及其家庭,思考如何更好地转化他们的能力,以服务于有意义的就业和工作,希望让他们过上更快乐、更健康、更有意义、更安全的生活。面对如此重大的社会责任,也许我们应该像作者东万一样问自己,“20年后我会后悔今天做的事吗?”
无论是2011年英国人亚当·范因斯坦(Adam Feinstein)写的《自闭症的历史》(A history of Autism),还是2015年下半年和2016年初不到6个月出版的两本超过700页的美国畅销书《神经部落》(Neurotribes,Steve Silberman)和《一把不同的钥匙:自闭症的故事》(John Don Van,Caren Zucker)都提到,在过去的80年里,科学家的研究数次误入歧途,误导和损害了许多自闭症患者及其家庭的生活。20世纪40年代末,美国精神病学家声称他们找到了自闭症的病因:无情的父母,尤其是母亲,缺乏对孩子的爱。就连最早研究自闭症症状的少数精神病学家之一利奥·肯纳(Leo Kenner)也一度放弃了自己最初关于自闭症是天生的理论,转而认同后来被称为“冰箱妈妈”的假说。在20世纪50-60年代,当这一假设流行时,儿童被送往感化院,遭受电击、体罚、迷幻药等。以善意的名义,而情况却极其悲惨。
在第一个看似“与国际接轨”的名词下,讲述了中国的故事,总结了中国的实践,宣扬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理念。所以郭医生的讲座非常接地气,在自闭症家长中反响热烈。实践雄辩地证明,孩子可以也愿意做家务。能拿出来在生活中学习,愿意在生活中学习”,这对父母是多么大的鼓舞啊!。

- 发表评论
-
- 最新评论 进入详细评论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