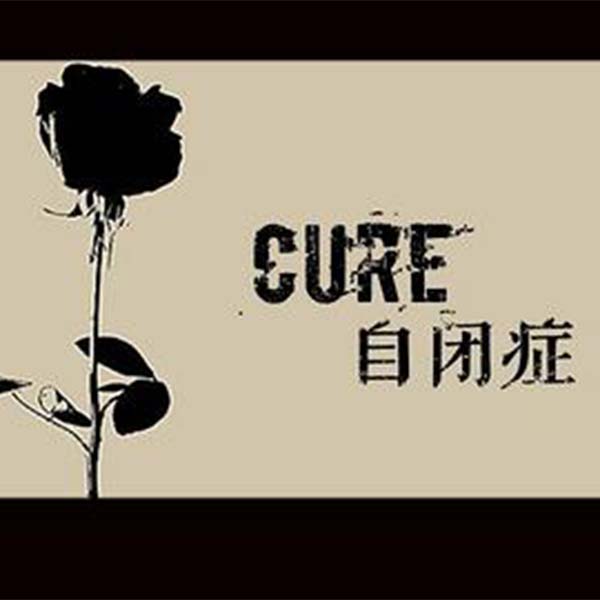自闭症儿童家庭的家庭信念探索与社会工作干预——以青岛XFZJ自闭症康复研究所为例 {智力发育迟缓}
“我曾经接触过一个家长,她为她和孩子的未来描绘了一幅美丽的画卷,一个安静的乡村,一个小房子,和儿子平静的生活,却从来没有提到过她的配偶。我以为她是离异家庭,其实不是。我和其他家长都向他暗示过,应该让他父亲参与进来,但是这个强势的母亲不听任何人的意见。我感觉她可能会把孩子当成私有财产来保护,连配偶都不能进入他们的世界。”(夏老师)
家长一般都希望孩子能接受融合教育,即安排在普通班,有专门的老师根据孩子的不同情况进行指导,尤其是一些高功能自闭症的家长。在
中
本研究主要关注自闭症家庭的父母、自闭症者对自闭症来源的认知、他们在儿童发展不同阶段的信心和期望,以及社会角色的赋权(如父母在养育子女过程中的权力分配和责任承担)。进行研究,探索自闭症家庭信仰体系的特点,分析形成这种信仰体系的因素的成因,提出社会工作的干预模式。
“我当时没有和老公商量就辞职了,因为我觉得孩子比工作重要。后来有了演技,贝爸也支持我的想法。毕竟他挣的比我多。他是个男人,可以去任何地方,但我不能离开小北。我个性很强,我认为我可以独自抚养这个孩子”(马贝)
(Jason Neely,Ellen Amatea,2012)在自闭症母亲的育儿压力研究中发现,孩子的母亲会对孩子的状况表现出深深的自责。这种自责导致母亲全身心投入到孩子的治疗中,缺乏自己的私人生活时间和与配偶的互动。
至于自闭症的成因,可以说爸爸的观点比较客观。尤其是那些天天致力于孩子康复训练的爸爸们。可以看出,参与育儿护理的父亲在对孩子自闭症的原因进行归因时更加理性,他们更倾向于解决问题。
“我们的孩子属于阿斯伯格,记忆力特别好。之前在台湾省看到一个小孩也是这种情况。他只是去医院管理档案。我当然想让他这么做,但是现在看来上学很难。我怎么敢想工作?”(奇奇的妈妈)
在父母的主观观念中,关于自己在照顾孩子中的家庭角色和家庭责任,父亲承担主要照顾责任的家庭强调男性的责任和担当,但父亲一般期望与配偶合作,愿意与配偶分担责任。然而,在母亲承担主要照顾责任的家庭中,母亲承担抚养子女的责任。母亲在对自己角色的认知中,强调“母亲”的角色,弱化“妻子”的角色。至于照顾孩子的责任,母亲不倾向于委托给父亲。此外,有些家庭长期分离。母亲基于实际情况,认为配偶对孩子的情况了解不够,拒绝配偶参与孩子的抚养。
“零拒绝”规则于2008年出台。但现实中,普通学校直接拒绝家长的情况并不少见。一些学校考虑到法律规定,通过频繁找家长或拒绝陪同的方式给家长施加压力,迫使孩子自愿退学。被拒绝后,家长关心的是可行性和后果,很少和学校争论。
在这种情况下,主要承担经济责任的配偶因为没有时间陪孩子而“一边倒”,而负责照顾的父母会因为配偶不了解孩子的情况而剥夺配偶参与孩子生活的机会。这种片面的家庭责任也会影响自闭症家庭的家庭信念,使得主要照顾者的个人信念取代了家庭信念。
从常态化理念的实践来看,国内常态化实践是西方模式与国情相结合的产物。以随班就读特殊教育模式的发展为例,随班就读模式的本质是一种务实的分班模式。不仅要让自闭症儿童以合理的方式融入社会,让他们与同龄人接触,加强对他们社交能力的训练,而且在社会对自闭症的宣传和认识上也不能流于表面。让大众真正了解自闭症的外在表现和成因,在对待自闭症儿童时能够有更多的宽容和接纳。
(Flippin,Michelle,2011)认为在自闭症儿童的康复过程中,父亲是不可忽视的,他们比母亲更有决断力和执行力。父亲的参与有助于孩子社交能力的发展,为家庭注入活力,形成家庭应对压力的应对机制。
首先要把握双向视角。在建立家庭信念的过程中,我们应该首先认识客户。父母是家庭信仰的主导者和接受者,而自闭症患者是福利的接受者。因此,在建立家庭信念的过程中,不仅要关注自闭症患者的需求,在自闭症患者不同的人生发展阶段对其进行规划和支持,还要作用于其家庭,让家庭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积极应对问题。
无论是普通家庭还是自闭症家庭,在孩子的日常抚养中,总有一方。但是,自闭症家庭有其特殊性。因子女日常康复需要,夫妻一方必须全程陪伴子女,承担抚养责任,另一方配偶承担家庭经济来源。家庭疗法认为子系统的边界是规定谁可以加入以及如何添加其他人的规则。通俗地说,纠结和疏离指的是一种交流方式,或者说是对某种互动和类型的偏好,而不是好的功能和紊乱之间的数量差异。大多数家庭都有纠结的子系统和疏离的子系统。在孩子小的时候,母亲和孩子的子系统可能倾向于纠缠在一起,而父亲会处于离孩子很远的位置;母亲和年幼的孩子可以如此纠缠,以至于父亲成了局外人,而父亲和年长的孩子关系更密切。当孩子长大,最终开始与家庭分离时,父母与孩子组成的子系统就趋于疏离。然而,如果家庭功能在极端情况下运作,它表明可能发生发病的地区。比如由母亲和孩子组成的高度纠结的子系统,会排斥父亲,让他极度疏离。由此造成的对孩子独立性的损害可能是症状发展的重要因素。
“当我们的父母玩得开心的时候,就逐渐形成了父母的圈子。周末,他们带着孩子出去郊游,去海边。虽然我们人不多,但是父母都是一颗心。有困难时,我们都互相帮助。有时候我们坐在一起互相安慰,聊些伤心的事,或者该怎么办。”(奇奇的妈妈)
3)优先级:对父母在家庭中角色和责任的认知。
“我有两个孩子。现在我告诉陶涛的妹妹长大后要照顾她的弟弟。我只是害怕我们走后会有人来照顾陶涛。”(陶涛的母亲)
随着随班就读和融合教育的发展,一些普通学校接受了自闭症儿童。然而,虽然随班就读和融合教育的形式得到了发展,但实际操作的支持系统尚未建立。学校没有具有特殊教育背景的教师,没有为特殊儿童设计的资源教室,这给自闭症儿童的融入带来了很大的障碍。
在认知导向的家庭治疗模式中,首先阐明父母对自闭症儿童起源的认知。在以家庭结构为导向的家庭治疗模式中,关注的是家庭权力的互动过程。导致家庭决策权过于集中在父母一方,家庭决策过程“一边倒”。夫妻双方都过于关注孩子的问题,父母的作用被加强而夫妻的作用被忽视。家庭治疗师可以帮助家庭了解自闭症,明确父母在孩子不同发展阶段的期望,帮助父母以积极的态度认识自闭症儿童,认识他们在家庭中的角色和作用,在孩子养育的过程中进行合理的、分阶段的参与。(张伟,杜,2013)孩子父母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优先事项的变化会影响他们看待孩子、家庭和自己的方式。积极的信念体系可以让他们更好的适应生活。在心理干预中,要注意评估儿童家庭的信仰体系,尊重和支持其家庭;通过与父母讨论他们的价值观和优先考虑的事情,孩子们会感到被理解;干预者可以基于评估以更智能的方式提供个性化干预,并增加干预的有效性。同时可以让家长了解信仰体系的重要性,促进他们对自己信仰体系的反思和调整。
在就业方面,父母对子女的期望值相对较低。总的来说,采访中的家长都是基于自己的职能为孩子的就业做规划,谈就业。高功能自闭症的父母往往能够结合孩子自身的能力从事相关行业,如经营个体店铺、管理仓库、卫生保洁等。家长们也表达了他们改善自闭症儿童就业体系的愿望。没有制度保障的就业欲望也成了天方夜谭。
(李丹,2003;黄,2009)发达国家自闭症照顾者的社会支持水平相对完善。一般康复机构和社区都会为家长提供正规的互助组织。互助组织有明确的目标和固定的成员,提倡父母双方参与。他们将定期开展互助活动,以缓解父母的育儿压力,获取新技能,扩大社交网络,增强同伴支持。然而,在mainland China,上级组织往往是非正式的,即以“小组”的形式出现。这种非正式组织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自闭症照顾者的日常育儿压力和焦虑,但缺乏由专业社工和心理咨询师引导的家长组织来排斥家庭中的另一位家长,不利于自闭症家庭积极家庭信念的构建。非正式互助组织有自己独特的组织信念。如果组织信念是积极的,它可以帮助父母建立健康的家庭信念。但如果组织里长时间的讨论话题过重,也会对家长的信念产生负面影响。
本文通过对自闭症儿童家庭信念的分析,揭示了父母如何在与社会环境和同伴群体的互动过程中,内化外部信念,建立家庭信念。通过对家庭信念的探索,作者希望展示父母个人信念与家庭信念的关系:首先,自闭症儿童的日常教养和社会融入不仅需要积极的治疗,还需要积极的家庭信念来支持和引导;其次,家庭信仰需要建立在社会接受的基础上;只有从社会制度、政策、社会环境等方面扶持自闭症患者及其家庭。,才能真正增强他们的家庭信念,促进自闭症患者的社会融入。
“非正常化”的思想来源于“正常化”的延伸概念。所谓“正常化”(Nirje,1994)“就是将残疾人和智障者纳入主流生活方式,享受正常生活条件的思想。”正常化的概念强调尊重残疾人的个人权利和社会权利。(纪磊,2002;卡姆,2003年,王芳,2006年;许婧,2007年;周,张俊贤,黄玲,,2008;蒋,廖攀,2009)然而,在这一概念的本土化过程中,残疾人被视为由于孤立的特殊教育和社会服务的限制而被排挤到主流文化边缘的畸形社会个体,他们的行为需要被修正以符合社会的主流文化和价值观。在实践中,表面上是尊重平等,实际上是不断“变态”。这种社会观念会内化为家庭观念,使得父母在孩子的社会融入过程中异常敏感。别人的一个眼神会触动父母内心想要保护孩子的欲望,进而引发矛盾。
“老师也不理他,跟我说你孩子自闭,会影响其他孩子。我之前也签过协议,如果我们的孩子对其他孩子造成任何伤害,就必须离开公园。我当时觉得被侮辱了。后来孩子不识字,我就离开了公园。”(欣荣的妈妈)
家庭信仰是家庭基于社会文化和社会价值观的整体生活态度、心理和精神状态。家庭信仰可以通过家庭文化和角色的相互作用代代相传。在家庭环境中,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和目标会影响孩子的发展。家庭信仰是夫妻双方通过对家庭事务和家庭问题做出价值判断而达成的共识。家庭信念的发展变化可以影响家庭成员的行为和认知。(Ransom,Fisher,& Terry,1992)家庭信念系统主要包括三个部分:
“我要对我孩子的病负责。我弟弟的孩子也是自闭症,症状比我严重很多,说明我的基因有问题。我对不起他的父亲……”(凯瑞的母亲)
“其实,我的心很敏感。有些自闭症儿童根本看不出来。跟正常孩子一样,贝贝就是没办法。有一次在一家家纺店,他穿上鞋踩了人家的床,把店员气坏了。我得向别人赔罪。其实我不怪人家。当人家像正常人一样看着你的孩子时,做出这样的举动是很不礼貌的。你跟他解释他们根本不懂,或者说这个社会真的懂自闭症。(马贝)
(李,2005)米兰的系统家庭治疗理论认为,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独特的家庭信仰体系,这是一个随着家庭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消极的生活事件可以使一个家庭决定采用积极或消极的信念系统来应对,而积极的家庭信念可以指导家庭成员应对创伤性事件。
(格兰茨&约翰逊公司,1999年;金等人,2003年;Wright,1983)家庭信念可以给家庭一个积极正面的初始诊断期。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往往以治愈为目的,积极寻求彻底治愈孩子的方法。以后这种心理会伴随着孩子的治疗过程,这种观念会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不断调整,最后会变得客观现实。初诊阶段的家庭信念是希望与失望、理想与现实并存。
(杰森。尼利,艾伦。Amatea,2012)在自闭症儿童发展的不同阶段,自闭症儿童的家庭面临着不同的压力和困难。家长一般在初诊、上学和青春期感受到的压力最大。
16.李丹、丁,西方父子依恋影响因素及教育思想研究述评,《国外中小学教育》,2013年第3期。
首先,要成立一个由社工主导的正式小组,小组的专家顾问可以包括医生、特级教师、心理康复教师等。其次,组织和活动要以群体需求为导向,在孩子康复过程中为家长提供有用的信息;第三,完全互助替代部分互助,缓解家长精神压力,提升团体动力和活动保障活动的参与率和效果;第四,社工要作为资源协调员,协调身边的医疗、康复、特殊教育等方面的信息和技术支持,让自闭症儿童的父母能够互相帮助,顺利完成康复和社会融入。
在受访的自闭症家庭中,母亲从拿到孩子的诊断证明那一刻起,自责的心态就在心里滋长。在十个被采访的自闭症家庭中,母亲的回答倾向于在自己身上探究原因,比如孕期是否服用了不利于胎儿发育的药物,婴儿期是否没有和孩子沟通好,是否忽视了别人对孩子的提醒。这种自责有双重内涵,对孩子和配偶都是如此。
“现在我还没想那么远。现在我只能想,等他到了上小学的年纪,我们就回江苏。我是一名教师,学校和教育局关系密切。回去后我会向我们的教育局长反映,请他为自闭症儿童和特殊儿童提供更好的教育环境。现在正规小学都没有专门的老师,很难带孩子。”(嘉诚爸爸)
“家长早上沟通最多的就是今天上学路上跟谁打架。有的孩子行为有问题,人们看的比较多。如果父母接受不了,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欣荣的妈妈)
一个家庭的信仰不仅包括父母对子女教养的期望,还包括父母双方对自身社会角色的认知过程。也就是父母在抚养孩子的过程中,主观上认同了自己的家庭角色和责任。
(李丹、丁,2013)首先,中国父亲较少参与与孩子的游戏互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父亲的角色更多的是一种权威,父亲的任务主要是帮助孩子学习社会价值观,形成各种得体的行为;其次,中国人的性格特征在某种程度上与欧美人不同;此外,中国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的社会支持在养育子女方面可能会有更多的体现。
“未来是顺其自然的,只要他能学会一些基本的生存技能。我对他的期望特别单纯。爸爸现在挣得多了,等他恢复好一点,开个小店让他维持生计。”(妈妈大熊猫开开)
信仰体系由世界观、价值观和优先顺序组成。研究者通过对国外自闭症儿童家庭的个案追踪和定性分析发现,自闭症儿童父母所具备的许多积极特质,在缓解危机冲击、调节压力和适应健康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信念是其积极特质之一。金的研究指出,当孩子被诊断为自闭症时,孩子的父母会放弃对孩子未来的期望和梦想,将抚养一个残疾孩子视为改变一生的负面经历;但有了照顾孩子的经验,他们会重新审视自己的信仰体系,进行积极的重新架构。
塞利格曼通过研究“习得性无助”提出了“习得性乐观”,认为积极的情绪体验可以通过学习获得。积极的情绪可以扩大注意和认知的范围,增加快乐的精神;产生新的思想和行为,培养持久的心理、智力和社会资源。因此,关注自闭症儿童父母的积极情绪可以成为促进其心理健康的基础。卡尔霍恩和谢赫认为,专业人员应该调整个人的心态以促进他们的成长,并提出识别个人的成长领域可以使他们摆脱自己的负面循环;因此,让孩子的父母分享他们的受益感和他们积极转化的结果是非常重要的。孩子父母的积极品质,如耐心和爱心,可以成为他们宝贵成长的开始。人们认为,父母自身的潜在视角可以帮助他们通过自我认知发展合理的应对机制,从而成为他们胜任照顾儿童的驱动力。
“我带他去了儿童医院,医生说是解体。当时真的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就觉得自闭症是一种病。如果你生病了,你可以治疗它。治个一两年就好了。后来我在网上查了各种资料,没有想到孩子得了绝症。父亲告诉我,我会花光所有的钱给孩子治病。后来这两年,我了解到解体是自闭症最严重的一种,但我还是抱有一些希望,希望有一天会好起来。”(小北妈妈)
“现在我已经和我们的大学同学和以前的同事失去了联系。说实话,我不去年度同学会,也不好意思去。我只是觉得在我们这个年纪,大家都是坐在桌边聊孩子,别人问我我也会说,但是我很不喜欢他们同情的眼神。慢慢的就没人问了,我也觉得没必要在一起了。你告诉人们他们不理解。”(欣荣妈妈)
父母对养老的想法,如果母亲承担主要照顾责任,他们会从更长远的角度考虑子女养老问题,而父亲承担主要照顾责任,对子女养老问题考虑不多。但双方家长普遍提到,子女未来照顾老人不应只是家庭责任,更期待政府福利责任的完善。
“我觉得作为家里的男人,我应该承担这个责任。我感觉在孩子的恢复上,比如感官训练,这些都是需要实力的,男性在这方面价格比较有优势;第三,我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都不错,经得起风浪。第四,在儿童语言方面,因为我是语文老师,所以擅长这个。”(家庭成为父亲)
“贝贝两岁前我在外地工作。为此我自责了整整一年。今年我每天晚上都睡不着。我觉得是因为他小时候我不在他身边,让他爷爷奶奶照顾他。”(马贝)
“我在这里,当然由我负责。我不在,但还是希望政府管管。现在没人管了。让我们一步一步来。我没想到有那么远。”(子涵的爸爸)
“我觉得孩子的妈妈很久没有出来了,直到现在她都不敢面对孩子。但不管怎样,这个病总得治吧?总得有人带他去治疗。”(子涵的爸爸)
基于家庭发展的视角,结合家庭需要关注人格保护的需要;重视自闭症儿童的早期筛查和诊断,为自闭症儿童的早期筛查、诊断和干预提供资金支持和服务保障;完善自闭症人群教育就业政策和服务体系,根据生命周期理论和家庭周期理论构建自闭症人群服务需求图谱,构建各阶段保护政策和服务模式。还要在政策制定和服务提供上形成协同工作机制,为自闭症患者及其家庭提供无缝的政策链和服务圈。形成从筛查-诊断-早期干预/康复-学前教育-学龄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就业服务-成人照料和社区服务-寄养等服务体系。根据自闭症患者的生活发展需求。
父母的压力不仅来自于养育过程中身体上的疲惫,更来自于期待孩子上进的心理焦虑。这些压力和焦虑也来自于现有不完善的安全体系的不安全感。从最初诊断时不知道如何界定孩子的病情,制定治疗方案,到幼师对孩子缺乏个性化、针对性的教育和训练,再到上学时间“零拒绝”制度的失效,往往要付出高昂的入园费才能进入一所正常的小学。之后,成年人的就业和养老不断向父母的信仰体系注入负面信息,
“你想想,我80岁死,他也快50岁了。我们一起走吧。你没有养过孩子,你没有养过自闭症的孩子。你不知道这里的困难。真的很难。”(马贝)
“那时候孩子妈妈总觉得孕期感冒可能不吃药。虽然她妈妈是医生,但这个问题还是困扰了她一年多。后来,我们都自我解脱了。有了这个孩子,就要好好教育他,好好抚养他。后来通过查网上资料和书籍,觉得这个病的病因很复杂,不应该简单说是什么原因。与其自责,自怨自艾,不如趁着时间,带着孩子好好恢复。”(家庭成为父亲)
家庭中的问题不能局限于家庭内部的考虑,家庭的信仰是社会普遍价值在家庭中的体现。自闭症家庭的家庭信念受到社会信念和组织信念的影响。可以说,自闭症家庭的家庭信念是随着自闭症患者的社会融入过程而变化的。
15.李丹,2003,自闭症儿童回归主流社会的基本条件,第6期,中国特殊教育。
22.周,张俊贤,黄玲,,2008,残疾人体育与社会公平,武汉体育学院学报,42 (8),22-25。
18.纪磊,2002,常态化理念下的变态实践——智障儿童“常态化”过程分析,北京大学研究生学报,(4),96-114。

- 发表评论
-
- 最新评论 进入详细评论页>>